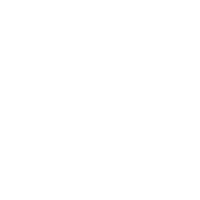
沈睿平虞汐(虞汐沈睿平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(虞汐沈睿平小说全文免费阅读)沈睿平虞汐最新章节列表笔趣阁


一个跟老婆结婚没多久的大学老师,身体没毛病,正是年轻力壮,但夫妻生活却一直不和谐。只能因为,他是个彻头彻尾的“狗”。“亲。”他捧起我的脚,像捧着件极其珍贵的艺术品,小心翼翼凑到脚背一点点亲吻。我的视线移到他的下半身,薄薄的布料被液体浸湿,有一小块暗色。我嗤笑:“真是条好犬。”得到夸奖的男人亲得更加卖力,我却突然抽走,把脚踩在他的肩膀处轻踹过去,他顺势向后倒。
“你要是再学不会怎么服从指令,就收拾衣服,滚蛋。”
我的声音很轻,软声细语,但跪在地上的男人听后却身子颤抖。
房间里没开灯,点了盏红烛,有种情迷意乱的暧昧感。
我抬脚,脚趾缓缓蹭过他的喉结,脚尖轻轻勾起下巴。
男人有一张清秀干净的脸,平时走在路上绝没有人能看出来,这样一张脸下竟然隐藏着特殊癖好。
除了我,圈里的顶级女王。
红烛摇曳,光照在薄纱床幔上,纱影随着光晕轻晃,让我曼妙的身姿增添几分朦胧魅惑。
纤细的手臂掀起床幔,盖在肩膀的外套滑落,露出光滑细嫩的皮肤,春色难遮。
男人看得愣住,他没想到刚刚言语强势压迫感极强的女王,竟是这么妩媚勾人。
看吧,你也不像你老婆说的那样废物。
一个跟老婆结婚没多久的大学老师,身体没毛病,正是年轻力壮,但夫妻生活却一直不和谐。
只能因为,他是个彻头彻尾的“狗”。
“亲。”
他捧起我的脚,像捧着件极其珍贵的艺术品,小心翼翼凑到脚背一点点亲吻。
我的视线移到他的下半身,薄薄的布料被液体浸湿,有一小块暗色。
我嗤笑:“真是条好犬。”
得到夸奖的男人亲得更加卖力,我却突然抽走,把脚踩在他的肩膀处轻踹过去,他顺势向后倒。
男人的眼神始终在我身上,迷离却色情,脸上因为兴奋还染着红晕。
我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,从床边站起身,高高在上地俯视他。
被欲望支配的动物,真是低级。
我用脚尖踩在男人的腹部薄肌上,慢慢往下滑。
一小时后。
我走出调教室,他的老婆已经在隔壁房间等了很久,也透过单向玻璃看了许久。
“看清楚了吗?”
女人红着脸点头,我回头看着被绑在凳子上浑身赤裸的男人,说到:“已经结束过一次,现在最少要休息二十分钟,听明白了?”
“知道了,谢谢您。”
我把用过的皮鞭递给她,女人双手捧着接过去,我没看错,她在握住皮鞭时,脸上除了羞涩,更多的是兴奋。
男下女上,我唇角勾起一抹微笑,看来他们以后的生活会和谐很多。
监控室里,我站在屏幕前点了支烟,看着各个房间的男女,或者男男,或者女女。
他们有的赤身裸体相互纠缠,有的高高在上,让另一个跪地为奴祈求怜爱。
情欲满屏,春色无限。
我没防备,一只手从我的背后伸过来,掐在脖子上强迫我转头,没等看清脸,柔软触感就贴上嘴唇。
但仅一秒,就被我猛地吹进口腔的烟气呛到,男人松开我,侧头剧烈咳嗽。
敢这么做的只有一个人。
“沈睿平,你有病?”

人气小说《咬红杏》由知名作者佚名倾心创作的一本灵异风格的小说,男女主角是咬红杏,文中感情叙述细腻,情节跌宕起伏,却又顺畅自然。下面是简介:“那是州府大人家的千金小姐张明瑶,平日她都眼高于顶不屑与我们这些商贾来往,今日为了那位裴公子,竟也自降身份来了。”宾客都聚在张明瑶身边,吴芳妍乐得自在,见到姜媚立刻过来与她说话。姜媚收回目光,轻声道:“裴公子那样的人,自然不乏爱慕者。”如果这位州府千金能博得裴景川的欢心,裴景川说不定能放过她。这个念头刚从姜媚脑子里冒出来,她便听到吴芳妍压低声音、神神秘秘地说:“瀚京美女如云,寻常姿色如何能入贵人的眼,而且听说裴公子已经有心上人了,今日张明瑶就是在模仿那位的打扮呢。”

火爆新书《沈知夏谢司聿》是作者倾心创作的一本都市风格的小说,这本小说的主角是沈知夏谢司聿,情节引人入胜,非常推荐。主要讲的是:这次不等他再说话,我就回屋了。依旧是背对沈知夏那边躺下,然后我拿出手机,只退了沈知夏的那张票。白沙湖很美,我一个人去,就可以独享这份美丽。看了眼票上的日期,我惊奇地发现那天竟正好就是沈知夏要结婚的那天。8月15,还有20天。那就在那天结束吧。我收起手机,合上了眼。不知道沈知夏是什么时候回屋睡觉的,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,身边已经没了他的身影。

徒留一捧白玫瑰,被风扬起是著名作者小说作品里面的男女主角,这本小说文笔情丝顺着、笔尖流淌,酣畅淋漓,感觉身在其中。一起来看看小说简介吧!就在她濒临窒息的时候,脖子上却明显一松。苏乔珺没了力气,跌跪在地上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傅泽年脸上闪过一抹异样,但很快又消失,一句话再次将她判了死刑:“你要知道,你是在给青月赎罪,你现在变成这样,都是你应得的!”苏乔珺抿着唇,低下了头,她现在说不了话,只能发出一些气音,她闭了闭眼,不再辩解:“好。”极轻的一句话消散在房间里,落在傅泽年心上,让他愈加烦闷,不再回答,兀自离开。

小编最近看了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说《戚意晚陆江艇》,是佚名所写,书中主人公戚意晚陆江艇精彩故事:三四个黑衣人看见他之后走上来将他围住:“少爷,请跟我们走一趟吧,先生和夫人在等您。”陆江艇其实早料到这一天的到来,因为从两个月前开始,陆母就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回家。她说:“我们约定好的五年,现在时间到了,你玩的也够久了,该回来了。”十八岁那年,陆江艇执拗的想要学法,不想走家里安排的道路。闹了很久,陆父和陆母松了口。他们答应让他学法,甚至可以多给他一年做律师的工作,但条件是所有花费都不能依靠家里,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能和家里开口,并且五年后就必须回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