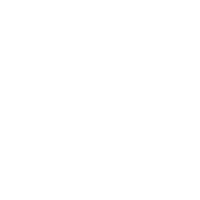
资讯


|孟欢沁心觉好笑。她原本也没有大闹婚礼的想法,只想见一见老太太。孟雪薇不过几句毫无根据的话,便又让她成了众矢之的。既然他们非要这么想,那不闹一闹,倒还要让人失望了。她牵了牵唇,弧度嘲弄:“许世子不必误会,我对你本就没什么爱慕之心,当初答应同你定亲,也不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现在你要娶侯府真千金,我亦只能祝愿。”听见这话,许承光愣住了。她说……对他并无情意?他藏在袖中的拳头顿时握紧,指甲几乎深陷长相。

|旁边的仆人听他这么说,毫不犹豫上前架起孟欢沁,想将她拖进侯府。“欢沁小姐,世子管教您,您就老实受着,您若是扰乱婚礼,惩罚怕要比现在还重百倍,世子对您,已经算是心慈手软。”孟欢沁看着仆人们的凶恶嘴脸,还有孟恒志冷硬的脸,心终于彻底冷下。早就看明白了的事情,为何之前她还报了那么一丝丝期待?她自嘲牵了牵唇角,语气凉薄:“刚刚那一跪,我跪的是老夫人从前的疼爱庇护,而今,世子没有让我罚跪的资格。”孟恒志怒极

|天衍州。江家议事殿。“江青禾!若不是你总喜欢惹是生非,少主怎么会变成这样?”“青禾,少主为救你,修为尽毁,金丹破碎,你就该主动拿出凤血涅槃果救人……”“青禾,你听话一些,乖乖交出东西。”……凤青禾刚醒来,就感觉脑瓜子嗡嗡的。像是误入了菜市场。凤青禾思绪混乱,只来得及抓住‘江青禾’这个名字。那本《龙傲天成神记》中,男主江青枢早死的姐姐就叫江青禾。这个江青禾虽然死的早,但后期也没少挨骂。因为江青禾活着

|“姐姐,跟我回江家吧,我会让父亲消气的。”“是江明远让你来的?”凤青禾此话一出。江青枢看向凤青禾的眼神骤然冰冷起来。江川一脸怒意道:“青禾小姐!那是家主,是你父亲,你怎能直呼其名?”凤青禾一个眼神都没给江川。这个人对原主从来都是横眉冷对。她已经离开江家,想怎么称呼江明远,就怎么称呼。不过看江青枢这个样子,应该是不知道那处小秘境被她搬走了。也对,有关江家底蕴的秘境,肯定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不然整个江家

|落霞谷入口。出现了两个人。“少主,落霞谷很危险,若是家主知道你偷偷来这里,肯定会担心的……”江青枢声音温和道:“我们不去中心区域,不会有什么危险。”他有不得不进去的理由。师尊已经推演出姐姐就在落霞谷。他要将进去带她回江家。从姐姐离开江家后,他就感觉不到她的气运了。若是一直这样下去,他和她之间的气运线会断掉,他将无法吸取她的气运。江青枢脑海浮现一句话,“青枢,登临神位的路注定鲜血淋漓,心不狠,终究会

|吼!——一道惊天震地的吼声响起。凤青禾看着下方那个朝天张开,明显等着被投喂的血盆大口,心情极度复杂。因为她就是对方等着吞入腹中的食物。但她此刻的灵力已见底。连控制下坠速度都不能,更何况躲开……而就在此时,下方的血盆大口消失,换成另一张黑漆漆的大口。接下来,不过几个呼吸间,下方那张大口的样式换了好几个。唯一不变的就是大口张开的位置。凤青禾产生一种自己是个绝世珍宝的错觉。于是她果断选择用掉了最后一张隐

|凤青禾打开一看,眼睛都在发光。江家矿脉的地图!虚空石之灵:我要沉睡一段时间,你别死了。凤青禾看了看手里的地图,无比肯定虚空石之灵在关心她。一张地图,胜过一切口头上的嘘寒问暖。而就此时,凤青禾生出了一种如芒在背之感。她立刻朝危险的源头看去,和远处山峰上的一头壮硕……黑熊对上了视线。妖兽?!还发现了她。所以虚空石之灵最后那句话是在提示她……她贴有隐息符,矿脉镇守者都没发现她,这头妖兽竟能找到她,那对方

|江明远盯着空空如也的传送阵,剩下的话卡在喉间,愤怒的表情僵住。这怎么可能!上古束灵阵下,一切传送手段皆是无法使用的。更何况还有九层塔殿自带的禁锢阵法……江明远走上传送阵,试图启动阵法。噗!——江明远当即喷出一口鲜血。江明远盯着传送阵上自己的血迹,眼神阴沉可怕,好似蕴藏着狂风暴雨。上古禁灵阵的效果还在。其他反伤阵法的效果也还在。所以不是这里的问题,一定是那个逆女干了什么。但他不可能为了去追那个逆女关

|第九章再次见到萧淮安,是五天之后。他穿着一身盔甲,身后是数十万精兵。而我们这边,不足一万。「今日我来,并非为了屠戮北疆余孽,只要你们肯交出笙雪,我便退兵不再来犯!」萧淮安骑在马上,慢条斯理地说着,眼中是势在必得的光。父皇怒目而视,手中弓箭应声而发。「无耻小贼,当年血洗北疆之仇,今日便用你的命来偿!」说罢,战鼓擂响,族人们嘶吼着冲向敌方。他们眼神中透着毫不畏惧的勇气,手中大刀挥舞。血腥气弥漫开来。没

|第八章「哗啦」「怎么会找不到!废物!」茶碗碎裂的声音伴着怒吼。这已经是大火后的第三日,萧淮安命人日夜挖掘,却没有我的半分踪迹。春桃也不见了踪影。他喘着粗气,像一头愤怒的狮子。「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!给我掘地三尺,否则,全部处死。」夏婉端着汤走来时,见到的便是他这要吃人的模样。脚步一顿,还是走了进去。「殿下,我做了补身的汤,您喝一碗吧。」「放下吧。」可萧淮安只是摆摆手,捏着眉心。夏婉眸光闪动,走到萧淮

|第七章醒来时,车窗外再不是闭塞的宫墙。大漠孤烟,长河落日,我再次回到了草原。父皇在一旁坐着小憩,只是轻微的响动便把他惊醒。凑着透过窗户的天光,我才看清他的模样。一头青丝已成花白,满脸的胡茬,左眼上戴着一个狰狞的罩子。我颤抖着抚上父皇的脸,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。「父皇。」一声呼唤仿佛说了千言万语。父皇喉结滚动,只是拉起我的手,不住地轻拍着。「回来就好,活着就好。」一路向北。阿爹和我说了很多。母后近些年

|第六章萧淮安满身的面粉,脸上还有几道烟灰。可他唇角带笑,这是近几日他最开心的一天。笙雪在等着他。可嘈杂的人声传来。「昭阳殿着火了!快来人救火啊!」手中的酥油茶掉落在地,溅了一身。萧淮安来时,昭阳殿早已是一片火海。四周一片嘈杂,可他恍若未闻。随手抓住一个下人,他泛红的眼眶映着火光,甚是可怖。「太子妃呢!昭阳殿的守卫都死哪儿去了!」下人瑟缩着,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。「奴才不知!奴才也是才被叫来救火的..

|第五章萧淮安开始夜夜宿昭阳殿。就像最开始我嫁入东宫时那样。每晚都将我紧紧地抱在怀中,给我唱家乡的歌谣,亲手为我熬制汤药。可我一夜白头,每日只是眼神空洞地望向远方,仿佛失去了灵魂的木偶,只剩一副躯壳。我看到他眼中的慌乱。听得到他满是柔情的话语。可,那换不回我的皇兄。终于像是被逼急了,萧淮安掐着我的下巴,眼中尽是癫狂:「姜笙雪!你连族人的生死也不顾了吗?还有,你的孩子。」我终于张开皲裂的唇瓣,嗓音沙哑

|第四章「好箭法!」被搀扶着来到猎场时,已经是人头攒动。夏良娣立在萧淮安身侧,满眼的倾慕。「殿下的箭术果真精准无比,一箭双雕也不在话下!」萧淮安再次勾弦拉弓,余光却瞥到了一旁的我。手中一松,箭矢掉落在地。夏良娣眸中闪过一抹狠戾,轻笑一声走过来,柔柔地挽上我的臂膀:「没想到我只是提了一句,殿下就真的把姐姐请来了。」她面上笑着,手上却暗暗用力,指甲深深陷进手臂的肉中。侧头凑近耳旁,语气中带着森森的寒意。

|北疆的朔风卷着黄沙呼啸而过,沈凝鸢站在城楼上,望着远处凯旋的军队。谢居安骑着黑马走在最前,银甲在夕阳下泛着血色的光。他手中长枪挑着蛮夷首领的金盔,身后将士们的欢呼声震得大地都在颤动。“夫人!”谢居安跃下马背,三步并作两步登上城楼。他铠甲上还带着未干的血迹,却笑得像个讨赏的少年:“为夫这仗打得可还入眼?”沈凝鸢掏出帕子擦他脸上的血污,指尖微微发抖:“莽夫,快让我诊断一下是否有伤。”他忽然抓住她的手按

|半年后。秋日的京城,落叶铺满长街。沈凝鸢正在庭院里晾晒药草,忽见谢居安疾步而来,玄色官服上金线绣的麒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他握住她沾着草药香的手:“边疆急报,蛮夷进犯。皇上命我即刻领兵出征。”沈凝鸢指尖一颤,反手握住他:“我随你同去。”“战场凶险……”“我是将军夫人,也是医者。”她抬头望进他眼底,“既嫁了你,生死都该在一处。”谢居安喉结滚动,终是将她搂进怀中。他铠甲冰凉,心跳却滚烫。……三日后,谢家

|喜烛高照,满室生辉。沈凝鸢端坐在铺着大红锦被的婚床上,指尖无意识地绞着嫁衣袖口。外院的喧闹声渐渐消散,只剩下烛花偶尔爆开的轻响。脚步声由远及近,最终停在门前。沈凝鸢呼吸微滞,红盖头下的世界忽然变得格外安静。“吱呀”一声,雕花木门被轻轻推开。“阿鸢。”熟悉的声音让她指尖一颤。盖头被金秤杆缓缓挑起,映入眼帘的是谢居安难得局促的模样。向来英挺的将军此刻耳尖泛红,喜服领口不知何时蹭上了一抹胭脂。“这是合卺

|夜色如墨,丞相府的灯笼在风中摇曳,映出一片朦胧的红。明日便是大婚,府中上下张灯结彩,喜气洋洋,可沈凝鸢的闺阁却格外安静。她坐在铜镜前,指尖轻轻抚过那件铺在床榻上的嫁衣——正红色,金线绣着鸾凤和鸣,华贵至极。这是谢居安特意命人赶制的,每一针每一线都极尽用心。“小姐,明日就要出嫁了,怎么还愁眉不展?”丫鬟替她梳着长发,轻声问道。沈凝鸢垂眸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,低声道:“只是觉得……有些不真实。”十

|两日后,文襄侯府。萧晏清攥着沈凝鸢的手腕穿过回廊,三百株新栽的桃树在暮色中开得正艳。每一株树下都挂着一块木牌,刻着她年少时写给他的诗。“阿鸢,你看……”他声音发涩,指向最大那株桃树,“我把你最喜欢的——”“砍了吧。”沈凝鸢抽回手,指尖发颤,“就像当初砍掉旧桃林一样。”一阵风过,花瓣沾满她鸦青鬓发。萧晏清下意识伸手,却在即将触及时被她避开。他掌心空悬着,嗓音发颤:“你当真,不愿给我个机会么?”沈凝鸢

|苏府门外。萧晏清一脚踹开苏家大门,手中攥着一叠信笺,眼底翻涌着戾气。苏雪禾惊慌失措地退后两步,却被他一把掐住下巴,强迫她抬头。“你胆子不小。”他声音冷得像淬了冰,“敢动她?”苏雪禾脸色煞白,强撑着冷笑:“怎么,萧世子后悔了?那你和她过完一夜后怎么——”“啪!”一记耳光狠狠扇在她脸上,萧晏清眼底猩红:“当日的催情药就是你下的?”苏雪禾身子一颤,眼神飘忽。他松开手,任由她跌坐在地,居高临下地睨着她,“

|姜挽晴哭得几乎晕厥,抱着孩子跌坐在沙发上,声音颤抖:“桑小姐……你怎么能这么狠心?他还是个婴儿啊!”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演技精湛到连周围的佣人都露出愤慨的神色。谢聿深站在一旁,脸色阴沉得可怕。他盯着桑宴宁,眼神里的失望几乎要溢出来:"你还有什么要说的?”桑宴宁抬起头,直直看向面前的男人:“不是我。”“不是你?”谢聿深冷笑,“针是从孩子衣服里找到的,而你是最后一个碰他的人!难道你要说是挽晴自己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