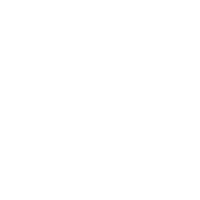
资讯


|第七章我立在屋顶,冷眼看着春桃悄悄离去的背影。「绿竹,去。」一条拇指粗细的竹叶青从檐角游下,悄无声息地跟上了春桃。两个时辰后,绿竹回到屋内,脸色煞白:「姑娘,那春桃去了清风观,见了观主。」「可看清那观主模样?」「那观主修为高深,我不敢靠得太近。」绿竹咬着唇,「但见春桃拿了许多符箓,还有一柄刻着镇妖咒的匕首。」清风观......想起孟承安的札记,我心中又是一痛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才勉强压下翻涌的情绪

|第六章新房内红烛依旧,喜气未散,却显得格外讽刺。我猛地掀翻桌上的酒壶,碎瓷四溅,划破我的手臂。「骗子!」数十年相伴,几百年执念,到底算什么?我疯了一般掀翻屋内陈设,扯下的凤冠砸到案几,咔哒一声,竟弹出一个暗格。一卷竹简滚落出来。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,这是孟承安的私人札记。我捡起竹简,心头莫名发紧。「永昌三年,绯绯为余挡箭,高烧三日。夜半探看,忽见青鳞覆面,方知非人。」手指不受控制往下翻,越看越心冷:

|第五章心脏仿佛被万根银针穿透,痛得几乎站立不住。「你再说一遍?」我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。孟承安却看也不看我一眼,转身将林瑟瑟小心安置在榻上。太医匆匆赶来诊脉,摇头叹息:「表小姐本就心疾缠身,如今又被人所伤,心脉受损,凡间药物怕是不起作用啊。」「那要如何救治?」孟承安急切地上前。老太医捋着胡须:「老夫曾在古籍中看过,蛇血温补。若能寻得百年,不,千年蛇妖,取其血连服三日,必可保表小姐无恙。」孟承安猛地

|第四章孟承安衣袍散乱,眉宇间尽是疲惫。目光扫过桌上的空酒壶,他眉头微蹙,温声道:「绯绯,昨日是我不对,瑟瑟到底是我表妹,我不能丢下她不管。」见我不语,孟承安俯下身,从袖中抽出一支青鳞蛇簪。轻轻插入我的发间。「当年你为了帮我凑齐进京赶考的盘缠,当了头上唯一一支发钗。」他指尖抚过我的发丝,眼中柔情万千:「如今,我赔你一支更好的。」「别生气了,好不好?」「孟承安。」我喉咙发紧,「你可知我昨日在喜堂上有多

|第三章又是这样。每一次,她都会用这种病弱可怜的模样,夺走所有人的怜惜。包括孟承安。意识到自己语气太重,孟承安缓下神色:「绯绯......」我打断他,几乎是从喉咙挤出一句话:「承安,继续拜堂吧,别耽误了吉时。」就在此时,林瑟瑟突然剧烈咳嗽起来,一口鲜血喷出,身子也摇摇欲坠。「表哥......我、我胸口好痛......」孟承安脸色骤变。他一把将林瑟瑟抱起,转身便往外走,只留下一句冰冷的命令:「仪式暂停

|第九节刘老汉出事师父一觉睡到了下午。醒来后,精神好了很多,开始在院子里踱步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把早上热好的饭端给他,他也没吃,只是看着手里的镇魂玉。“师父,你在想什么?”我问。师父抬起头:“你觉得,红丫头为什么那么在意这块镇魂玉?”“不知道。”我摇摇头,“可能……是她生前很喜欢的东西吧。”“不像。”师父摇摇头,“镇魂玉是用来镇压她的,她应该很恨这东西才对,可昨天晚上,她明明很想要回去。”“那……

|第八节红影我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想都没想,举起桃木剑就朝红色的影子砍了过去。桃木剑辟邪的,按理说对鬼魂应该有用。但砍在红影身上,却像砍在空处,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红影没理我,继续朝王老五飘去。王老五吓得瘫在地上,手脚并用往后退,嘴里胡乱喊着:“别过来!别过来!不是我动了你的坟!不关我的事!”红影越来越近,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和腐臭味扑面而来。就在这时,师父大喊一声:“着!”一张黄符从师父手里飞出,正好

|第七节准备回到王老五家,已经是下午了。师父把自己关在屋里,开始准备晚上做法事的东西。黄符、朱砂、桃木剑、罗盘,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法器,摆满了一桌子。他一会儿画符,一会儿念咒,忙得不可开交。我在一旁看着,不敢打扰。王老五端来晚饭,师父也没吃,只是摆摆手,让我们自己吃。我心里很紧张,不知道今晚的法事能不能成功。红丫头的怨气那么重,连镇魂玉都镇不住,师父能对付得了吗?“狗剩。”师父突然叫我。“师父

|第六节祠堂祠堂在村子中间,是个老旧的瓦房,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里面供奉着村里的祖宗牌位,阴森森的,平时很少有人来。不到半个时辰,村里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,挤在祠堂里,叽叽喳喳地议论着,气氛很紧张。师父站在祖宗牌位前,手里拿着桃木剑,脸色严肃。“安静。”师父说。祠堂里很快就安静下来,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师父身上。“大柱、二丫、栓柱,三天死了三个人。”师父缓缓开口,“死状一样,都攥着红丫头坟里的泥土,都

|“怎么了,师父?”师父没说话,用手挖了起来。泥土很松,很快就挖出一个小坑。坑里,露出了一块布。是一块红色的布,看起来像是新娘穿的嫁衣上的布料。师父把那块布拿出来,布已经很旧了,上面沾着不少黑褐色的泥土。“这是……”王老五看着那块红布,一脸疑惑。师父拿着红布,闻了闻,脸色变得很难看:“怨气很重。”“怨气?”“嗯。”师父点点头,“这坟里的人,死的时候肯定很不甘心,怨气都积在这布上了。”他把红布放回坑里

|第四节坟地第二天一早,天刚蒙蒙亮,师父就叫我起来了。推开房门,院子里的黑褐色泥土还在,被露水打湿,显得更加黏腻。王老五已经起来了,看到院子里的泥土,脸色一白:“道长,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?”“别管。”师父说,“带我们去村里的坟地看看。”王老五愣了一下:“坟地?去那儿干什么?”“大柱和二丫手里的泥土,是坟地里的。”师父说,“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王老五不敢多问,点点头:“好,好。村里的坟地在村后的山坡上

|黑暗。永无止境的黑暗。只有沉重的喘息声,和碎石簌簌落下的细碎声响,在狭窄、陡峭、不断向下延伸的金属通道里回荡。每一次呼吸都像吞下砂砾,带着浓重的土腥、臭氧和……自己鲜血的铁锈味。我几乎是拖着苏晚在前进。她的身体沉重得像一块浸透水的石头,大半重量都压在我没受伤的左肩上。每一次挪动脚步,都牵扯着右臂被电流灼烧的剧痛和手腕上那道狰狞伤口的撕裂感。虚脱和眩晕如同跗骨之蛆,疯狂啃噬着残存的意志。汗水混合着血

|黑暗。冰冷。窒息。狭窄的金属通道如同巨兽的食道,陡峭地向下延伸。头顶惨淡的应急绿光,像垂死萤火虫的眼睛,在湿滑冰冷的墙壁上投下晃动的、鬼魅般的影子。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土腥、臭氧,还有一种……类似高压电击后残留的、焦糊的金属气味。每一次呼吸,都像吞下冰渣,刺痛着虚弱的肺叶。我背靠着冰冷滑腻的墙壁,剧烈地喘息着。金属门外,陆天明那混合着怨毒与疯狂的恐怖咆哮和沉重的撞击声,如同闷雷般一下下捶打着耳膜和心

|**“吼——!!!!!”**咆哮!无法形容的咆哮!那不是野兽的嘶吼,而是无数种声音强行糅合在一起的、充满极致痛苦与怨毒的地狱哀嚎!它混合着金属扭曲的尖啸、肉体撕裂的闷响、还有……一种属于陆天明的、扭曲到极致的疯狂人声!如同实质性的重锤,裹挟着滔天的恨意,狠狠砸穿了研究所厚重的墙壁和金属门板,撞进这间尘封的核心实验室!轰隆——!!!整个空间都在剧烈震颤!天花板的灰尘、碎裂的灯管残骸如同暴雨般簌簌落下

|它醒了?它在呼唤?!锁好门!不惜一切代价!父亲最后的信息!充满了警告和绝望!他到底在指什么?!“门”在哪里?!“钥匙”是什么?!“容器”……又是什么?!巨大的谜团如同冰冷的潮水,瞬间将我淹没!我捏着这张仿佛带着父亲最后体温和恐惧的便签,浑身冰冷,大脑一片混乱。就在这时——诊所紧闭的铁门外,毫无征兆地传来一声沉闷的、仿佛重物落地的声响!咚!紧接着,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、如同巨大锉刀在粗糙石头上反复刮

|“东……西?”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,干涩得像砂纸摩擦骨头。苏晚平静话语里蕴含的冰冷信息,像一条毒蛇,缠绕上我刚刚因狂喜而滚烫的心脏,瞬间冻结了血液。陆天明没死。他变成了……“东西”?什么东西?!是人?是鬼?还是……一种本能的、深入骨髓的寒意顺着脊椎爬升。我下意识地伸手探向口袋——那个存放着最隐秘物品的地方。指尖触碰到一张折叠得异常整齐、带着硬挺棱角的纸片。是它。一直在我外套内袋里。我甚至不记得什么时

|冰冷。刺骨的冰冷,像是被塞进了冻肉库的最底层,连思维都冻成了冰渣。没有痛,没有光,没有声音,只有一片虚无的、沉重的、永恒的黑暗。这就是死亡吗?倒是比预想的……安静。陈远得意的狂笑,陆天明儒雅面具下的狰狞,蚀心灼烧神经的剧痛……这些最后的记忆碎片,在绝对的死寂里沉浮,像沉船的残骸,带着不甘的怨毒,却掀不起一丝涟漪。就这样结束了?像父亲一样,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某个角落,成为阴谋家脚下一块微不足道的垫脚石

|“闭嘴!”白浩雄厉斥,被白洛舟的话气得胸膛剧烈起伏。反复在心里默念这是自己亲孙子,才压下将白洛舟一掌拍死的冲动。白洛舟被白浩雄凌厉的眼神镇住,大气不敢出。白浩雄收回视线,朝六长老步步紧逼。“六长老,若你所言不假,何惧搜魂?”白优星皱紧眉,此时也觉白浩雄糊涂。时初她算什么,爷爷竟然要为了她寒对白家有重大贡献的六长老的心。她挡在六长老身前,企图唤回白浩雄的理智。“爷爷,你当真要为了她,做到这个地步吗?

|寒霜瞬间席卷整座小院,白优星手中冷剑破开霜雾,逼至时初命门。时初身周,雷霆之力蓄势待发。她漠然地望着白优星,她再前进一步,弥散在四周的雷霆之力便能将她击溃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一声厉喝传来。“住手!”渡灵境威压紧随而至。白优星的剑顿时无法再往前推进半分,笼罩在小院内的寒霜也立马消散。白苍崖、六长老、白洛舟皆被这威压逼得后退几步。时初见状,犹豫一瞬,最终还是收起了攻势,抬头看向院门口。匆匆赶来的

|听到这声“爷爷”,白浩雄心软得一塌糊涂。心里越发觉得亏欠。当年,是他错误的教育,才让几个儿子相互嫉妒,最后导致时初被恶意调换,失了双眼,在偏远的村落里艰难长大。他心疼她的遭遇,也明白她孤身一人回白家,他若不能成为她的依靠,她的余生会更加痛苦,甚至可能一步行错,踏上歪路。所以当决定接她回白家的那一刻起,他就暗暗发誓,他要用自己的余生去弥补她,给她最大的偏爱。毕竟是因为他的错误,才造成了她的苦难,若非

|时初看去,迎面走来的是个看上去三十出头的男人,穿着一身白袍,气质儒雅,带着书卷气。与他一起来的,除白洛舟外,还有一个紫衣少女,少女与她年纪相仿,都是十五左右,面容娇美,眉目间带着些倨傲。她一来,目光就锁定在了时初身上。这虽然是她们第一次见,但少女对她的敌意毫不掩饰。时初蹙眉,一个名字浮上她的心间。——白优星。那个顶替了她身份,在白家生活了十五年的少女。她没想到,她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回白家的这一路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