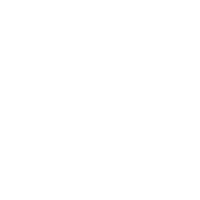
恰是玫瑰盛放时(米悠乐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(米悠乐)恰是玫瑰盛放时最新章节列表


庄宇勾了一下嘴角,回应了这个冷笑话。他斟酌了一下措辞,在米悠乐睡着之前尽可能用最简洁易懂的语句说:“你大姑,我妈,想让咱俩结婚。”米悠乐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,咕咕哝哝回了一句:“哦,知道了。”半晌,她终于醒了过来,眼珠子差点就要蹦出来:“你好好说,大姑让咱俩干嘛?”“结婚。”庄宇是收养的这件事,没几个人知道,米悠乐更是像被闷雷轰中了天灵盖,呆立当场。
“当一个人不喜欢你的时候,你的存在即骚扰,明白吗?”
庄宇撂下这句话,推开车门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江煦呆坐在车里,紧靠着并不算柔软的座椅靠背,直勾勾盯着庄宇的背影,直到他的背影,彻底和夜色融为一体。
最后这句话,精准命中了江煦强大心脏里潜藏的万分之一易碎区域。他并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对米悠乐来说,是不是已经构成了一种“骚扰”?
他莫名联想到了邸姗姗,不得不承认,庄宇说的对。
勇敢追爱必然是难能可贵的,然而,可贵的前提有一条,郎有情妾羞涩,才会在暧昧推拉之间火花四溅,一厢情愿地拽着对方的尾巴,尾巴会烂,也会被拖在地上疯狂摩擦。
只可惜,他并不能确定自己和米悠乐是哪一种,他可以单方面付出,但不接受两败俱伤。
他看了看表,快十一点,不算太晚。
车熄了火,才下车关上车门,江煦就拿出手机开始叫车,因为着急,脚下便生了风,平时五分钟的路程,今晚不到两分钟就走出了小区大门。
临近年关,代驾不好叫不全是借口,网约车难约也是真的。小区外的四向大马路上空荡荡,远处天际变得微红,有要下雪的迹象。
孤立无援中,一个小哥骑着共享小电驴从天而降,在不远处停了下来,弯腰锁车,跑进路边的便利店。再拎着袋子出来,小电驴已经无影无踪。
兔子急了会咬人,所以,江煦急了也会骑车。
风驰电掣间,他还不忘给米悠乐发个信息:别睡,等我,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。
家属院的几百扇窗户里,几乎都藏着或轻或重的鼾声,仰头看上去,仅剩一扇窗户还透着微黄色的光,那是米悠乐的卧室。
如果不是庄宇的去而复返,她也会熄了灯,埋在棉花被子里刷着千篇一律的短视频,每一条停留不过十秒。
十分钟前,庄宇打电话说,他有十分重要的事情,一定要赶在他妈妈,也就是米榕女士明天飞机落地前,当面告诉她。她撒娇耍赖打滚无果后,只好裹着浅蓝色的过膝羽绒服,睡眼朦胧地从五楼走下来,一屁股坐在了楼门前的椅子上。
十分钟后,庄宇还没有开口。
米悠乐兜里的手机震了震,是江煦火急火燎的信息,她没回复,反手按灭屏幕。此时此刻,她只想梦周公,像从大城市逃回草原牛马,珍惜每一秒原始的快乐。
她耐心告罄,发出最后通牒:“哥,你大晚上把我叫下来,是因为诺亚方舟要开了,你只有一张船票,所以不能告诉大姑是吗?”
庄宇勾了一下嘴角,回应了这个冷笑话。
他斟酌了一下措辞,在米悠乐睡着之前尽可能用最简洁易懂的语句说:“你大姑,我妈,想让咱俩结婚。”
米悠乐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,咕咕哝哝回了一句:“哦,知道了。”
半晌,她终于醒了过来,眼珠子差点就要蹦出来:“你好好说,大姑让咱俩干嘛?”
“结婚。”
庄宇是收养的这件事,没几个人知道,米悠乐更是像被闷雷轰中了天灵盖,呆立当场。
庄宇才几个月大,就被遗弃在米榕的小卖部门口。这些年,米榕夫妇对他很好,属于要星星还努力摘月亮的那类家长,除了物质不算富裕,也堪称是母慈子孝的当代演绎。去年,他父亲去世,米榕性格突变,把庄宇看做她生命里唯一的稻草,恨不得变成迷你手办,钻进庄宇兜里,生怕从此无依无靠。
米悠乐懵劲小了些,脑子清明了些,努力在迷雾里,把稀碎的线索勉强串成了线,总之是,米榕为了让庄宇不仅在户口本上作为一家人,更要在血缘上成为真真正正的一家人,而她,作为唯一拥有老米家纯净血统的传人,就是这个无可替代的纽带。
她不知道该哭该笑,所以表情变得很丑:“你妈真的,天才。”
那个“真”字发音,短平快,且弱。庄宇一怔。
对话到这里,忽然就停滞了。
庄宇再次陷入了沉默,他双手插进裤子口袋,仰头看月亮。路灯和月亮青黄交织的光把他映照得像幅笔调轻巧的油彩画。如果寻若楠在,她亮晶晶的眼睛一定舍不得从庄宇身上挪开一秒,会感慨,夜色中月光下这样仰头看月亮的庄宇真是个清俊儒雅的妙人。
但是,现在米悠乐不会这么想,想到寻若楠,她心口一阵阵的紧绷,这些年她打下的战利品还在寻若楠的公寓里托管着,她还指望回上海后,能好吃懒做求包养。
看月亮的庄宇听到米悠乐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后,转过头来,微笑着问:“小米,那你怎么想。”
他这副意味不明的微笑,直接把米悠乐吓应激了。
米悠乐蹭地一下站起来,怎么想,还能怎么想,在她的意识里,这比八点档的狗血剧还要狗血,自己的大姑撺掇亲堂哥来娶自己,封建主义也不能这么吃人,她嘴角一抽一抽地,一肚子的脏话堵在她的嗓子眼,随时打算喷薄而出。
她尽全力克制自己,只说:“包办婚姻,指腹为婚,近亲繁殖的封建时代,过去了,新中国了。”
在路灯的微光中,庄宇垂着薄薄的眼皮,忽的嘴角轻轻一翘,笑得有些似笑非笑的:“你怎么不问问,我怎么想的。”
他顿了顿,温声道:“我初中就知道这件事了。”
米悠乐连连忙往后退了两步,拉开了自己和庄宇的距离,这一刻,哪怕是自作多情地想偏了,她都必须立刻摆清自己的立场。
她眼神坚定,不留一丝余地:“哥,你永远是我亲哥。”
庄宇脸上的笑意逐渐扩大,伸手揉了揉她已经乱糟糟的头发说:“我来找你,是因为你大姑明天一早就来,我要在她找你之前,告诉你,让你做好心理准备。
“放心,咱俩一起对付她。”
庄宇的回答让她稍稍安了心。
她很想装作不经意地问一下:哥,你确定不会对我产生什么不该有的虎狼情愫吧。
可酝酿了又酝酿,终究还是没有足够勇气把这问题从齿缝里推出去。她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后面,哪怕万分之一自己不想听到的答案。既然对方看起来都如此坦然,自己又何必搞得一副天崩地裂的模样,拉出马脚出来现眼。
彼此无言的状态有些干巴巴的尴尬,米悠乐恭恭敬敬地把庄宇送到家属院门口。
夜晚的静谧让脚步声成了全世界唯一的响动。这响动像个结界一样,各自兜住米悠乐和庄宇,仿佛谁开口,都会回弹出一份尴尬。
直到载着庄宇的出租车轰鸣了引擎,才打破了那份唯一响动所构筑的结界。
米悠乐瞬间佝了背,沉沉的叹气,就这么一路叹到了楼下。
下一秒,她就应验了人一旦开始倒霉,就会有倒不完的霉。
江煦插着兜,在她家楼下来回踱步,四目相对的刹那,她愣了,江煦没有。
很明显,不管江煦是怎么把自己变到了这里,从他清澈且无辜的眼神中,米悠乐知道,刚才她和庄宇的一场大戏,他是唯一的热心观众。
她歪了脑袋,摇了摇头:“都听见了。”
江煦实话实说:“我来的时候听见你们对话内容,确实也不好插嘴,就在树后面站着听。”
米悠乐身体是静止的,思绪确实沸腾跳跃的,她说:“家丑不可外扬,我在想,不如灭口安心一些。”
江煦回了他一个假惺惺又有点皮的笑容:“其实还有一个办法,既然家丑不可外扬,那把我变成自己人就可以了。”
米悠乐心中一动,选择装傻:“难不成你是老米的私生子。”
江煦眉毛一高一低,不满的神色毫不掩饰地展露在高低眉间:“你以为少了个堂大哥,来个嫡亲小弟,什么脑回路。”
他说:“本少爷我就是来要个答案的。”
米悠乐扶额,该来的确实也躲不掉,只不过,她还没有想好答案。
还好,他下一秒就没了气势,小心翼翼地问道: “你说,我是不是在骚扰你?”
怎么停在这?!怕你不看了好看爱看,静等更新机会这不就从天而降了吗爱看,最好日更努力努力

主角叫萧熠声晏欢的小说是《萧熠声晏欢》,它的作者是佚名写的一本小说,内容主要讲述:清宁点着头,继续道:“王爷毁容那年,回府之后,将府中的铜镜全都砸了,从此王府不能出现铜镜。就连荷花池都填了,唯独那水榭留着,只因是端贵妃当年亲自监工的。”“荷花池都填了?”晏欢这才恍然,难怪她的梳妆台都没有铜镜。在王府那么久,真的没照过铜镜。她虽然有些惊讶,却能理解萧陆声。若是她毁容,肯定也没有勇气直面自己吧。清宁点头,“是,荷花池都填了,连院里那些水缸都常年盖着的,王爷不愿看到自己。”顿了顿,继续道“王爷今天在主屋里放了带铜镜的梳妆台,想着是因为王妃需要吧。”

主角是裴知颂苏尔尔的书名叫《裴知颂苏尔尔》,是作者倾心创作的一本影视同人类小说,小说中内容说的是:脏了的裤子在地上,她也不能捡起来再穿,下边一直是裸着的,直到裴知颂来敲门——“苏尔尔,你在里面很久了。”“哦。”苏尔尔双手攥着搁膝盖上,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她不说话,裴知颂就又喊她,“苏尔尔,我进来了。”“不要!”苏尔尔冲着门口喊。裴知颂刚拧开门把手,人就停在外面了。空气中多多少少有点血腥味,苏尔尔闻到了,她怀疑裴知颂也闻到了。她怎么这么倒霉呢。“苏尔尔?”

作者写的小说《江颖雯孟渝州》,主人公江颖雯孟渝州的故事精彩引人入目。还有母亲的死……写着写着,江颖雯的眼泪氤氲而出。渐渐打湿了面前的字迹,笔尖在信纸上划过,留下一串模糊的痕迹。她试图擦干脸上的泪水,但却像潮水般涌出,泛滥了她的心。江颖雯写了满满几大页,才停下来。她将信纸和证件装好后,再次走出家门。军区师长办公室。江颖雯将信封放到长桌上,对着厉师长郑重开口。“师长,孟渝州同志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不忠,我要和他离婚!”

岑渺渺陆知琛是作者岑渺渺陆知琛最新写的小说里面的男女主角。作者文笔不错,诗词功底丰富,文章结局很意外,千万要看完哦!内容主要讲述打开了日记本的第一页,就是一张我和陆知琛的婚纱照合照,虽然当时我们拍照的时候不是很心甘情愿的,但是现在看来,还是不错的。照片的下面写着一行字“只此一人,陆知琛”,我笑了一下,紧接着连着翻看了几页,看来陆知琛是有记日记的习惯,看了日记的前几页,我就已经笑的不行不行的了,前几页大致内容,写的是刚刚认识我,觉得我还不错,很安静的一个人,但是非常反对这种绑定婚姻,所以处处针对我,我心里想,看来他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。往下翻了几页,我的心越来越感动,日记内容,从我俩结婚当天他整蛊我,到我们回我家之前,所有我俩在一起的开心快乐的事,日记里写了这么一段话“抱着顺其自然心态的我,却在第一次亲吻她的时候,发现我居然喜欢上了她,看着她被我压在身下,却不畏惧的眼神,让我特别想占有她,不只是身体,还有她的心,我不能容忍别的异性出现在她的眼神里,她的眼神里,只能有我。”我把日记本合上捂在胸口,原来,他在那个时候,已经喜欢上了我。